韩非的冷峻与功利
韩非的思想,与儒、墨、道三家其实都有关联。
首先是老子的“冷峻”。老子是“无情无义”的。
他的观点,是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;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”(《老子·第五章》)。这是什么态度?是“冷眼旁观不动声色的理知态度”(李泽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)。这是老子的态度,也是韩非的态度。
因此,老、韩之“道”虽不同,其“冷”则相似。他们都是先秦诸子中最“冷”的,而墨子和孟子最“热”。热就充满理想,冷就面对现实;热就总想救世,冷就善于旁观。旁观者清,现实者直。所以,冷若冰霜之老、韩,就比侠肝义胆之墨、孟,更能直面惨淡的人生。

〇 李华摄影
其实韩非同样受到墨子的影响,这就是“功利”。韩非与墨子,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。当然,他们讲的内容并不相同。比如墨子讲“天下之利”,韩非讲“个人之利”;墨子讲“庶民之用”,韩非讲“君主之用”。但主张讲功利、讲实用,则是一样的。
因此,先秦诸子中,反倒是韩非对墨子有所同情。比方说,有人批评《墨子》没有文采,韩非就借他人之口为之辩护。
韩非说,当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,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媵女作陪嫁,结果晋公子喜欢媵女,不喜欢公主。楚国的商人卖珍珠,用香木做成盒子,还要“薰以桂椒,缀以珠玉,饰以玫瑰,辑以羽翠”,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,退回珍珠。
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形式如果大于内容,就会危害内容。
那么,是形式重要,还是内容重要?内容重要。内容为什么重要?因为有用。实际上,墨子的语言之所以质朴,就因为他担心人君“览其文而忘有用”,“怀其文忘其直”,这才故意不要文采(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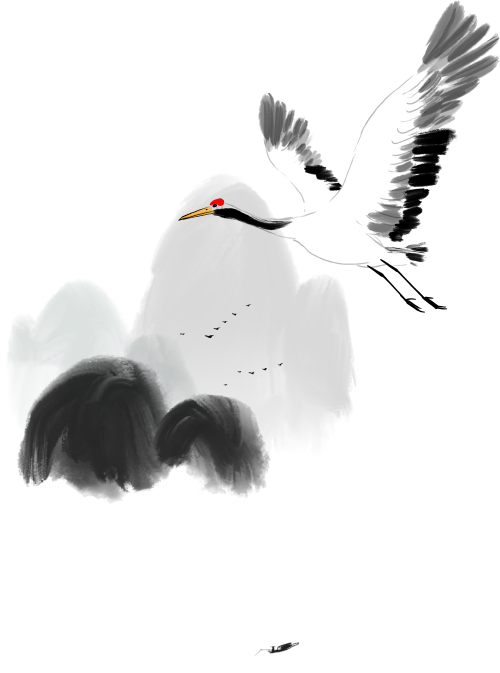
显然,韩非这是以功利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。内容有功利,形式无功利,因此要内容不要形式。或许有人会问,内容和形式,难道就不能统一吗?孔子认为可以,韩非认为不行。孔子为什么认为可以呢?因为在孔子他们那里,内容与形式,就像皮与毛。
据《论语·颜渊》,有人曾经问孔子的学生子贡:一个君子,有优秀的品质也就行了,为什么还要有文采修饰呢(君子质而已矣,何以文为)?
子贡说:老先生这话真是太让人遗憾了。质,就好比皮;文,就好比毛。皮与毛,都是不能少的。试想,如果去掉毛,那虎皮、豹皮,与狗皮、羊皮,又有什么区别呢?恐怕是“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”(鞟,音阔,去毛的兽皮)。
显然,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。没有内容,形式就没有必要;没有形式,内容也无法表现。君子之所以是君子,就因为他不但有优秀品质,而且有文采修饰。没有了文采修饰,作为虎豹的君子,与就像犬羊的小人,又有什么不同呢?

〇 李华摄影
韩非却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,内容与形式的关系,不是什么皮与毛,而是冰与炭、寒与暑。“冰炭不同器而久,寒暑不兼时而至”(《韩非子·显学》),怎么可能统一?
韩非还说,楚国有个人,卖矛又卖盾。卖盾的时候说:我的盾,什么矛都挡得住。卖矛的时候又说:我的矛,什么盾都刺得穿。有人说,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,怎么样?这人不能回答(《韩非子·难一》)。
同样,一个东西,你不能既要形式,又要内容。要了形式,肯定会丢了内容。秦伯嫁女贵妾,郑人买椟还珠,就是证明。
这就是韩非的矛盾论。“矛盾”这个词,也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。问题是这能证明什么呢?能证明人性是恶的。
在《解老》篇中,韩非说,礼乐,是人性的样子(礼为情貌者也);文采,是质地的装饰(文为质饰者也)。也就是说,人性是内容,礼乐是形式;人性是质地,礼乐是装饰。装饰的意义何在呢?遮丑。所以,“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,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”。为什么?用不着嘛!这就叫“其质至美,物不足以饰之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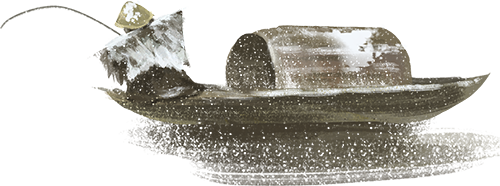
相反,如果必须装饰,离不开装饰,就说明它的本质有问题。这就叫“物之待饰而后行者,其质不美也”。人性既然需要礼乐做形式、做装饰,岂非证明人性有问题?而且,礼乐越是美好,岂非越能证明人心和人性是坏的?那么,礼乐这东西,是可有可无的呢,还是不可或缺的呢?儒家说绝对不能没有。
由此可见,在儒家那里,人心也是坏的,人性也是恶的。

〇 李华摄影
哈哈!这可真是“以子之矛,陷子之盾”,用儒家的砖头砸了儒家的脚。可惜,“矛盾”一词的发明权,是韩非的。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的逻辑前提,也是韩非的。孔子之徒当然不会认账。在他们那里,人情与礼乐,是皮与毛嘛!
不过,具有戏剧性的是,韩非的逻辑虽然是自己的,“性恶”的结论却是受了一位儒学大师的影响。谁?荀子。
荀子是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师,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。他是赵国人,名况,当时的人尊称他为“荀卿”。汉代的人,为了避汉宣帝的讳,称他为“孙卿”。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13年,卒于公元前238年,早年曾经游学齐国,三为祭酒,后来又到了楚国的兰陵县(在今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),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县令,著书立说,终老于此。韩非和李斯,就是他的学生。

〇李华摄影
儒家大师教出两个赫赫有名的法家学生,这事真值得琢磨。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,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巨子,荀子与孔子、孟子有什么不同。
最大的区别,也许就在人性问题。
我们知道,孔子教书育人做学问,是有所言有所不言的。比方说,不谈死亡,不谈鬼神,不谈天道,不谈人性。这一点,他的学生子贡说得很清楚。子贡说:“夫子之文章,可得而闻也;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
这里说的“文章”,就是诗书礼乐和历史文献。这里说的“性与天道”,则是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。诗书礼乐和历史文献,孔子说得比较多,学生们也听得到。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,孔子就不怎么说了。为什么不说呢?不清楚,反正是不说。
孔子不说,不等于孟子和荀子也不说。许多人认为,孟子和荀子都是谈人性的,只不过观点不同。孟子主张“人性本善”,这叫性善论;荀子主张“人性本恶”,这叫性恶论。不少哲学书都这么讲。其实这种说法可以商量。
我的看法是:第一,孟子并不喜欢谈人性,但又不能不谈。第二,孟子也不主张“人性本善”,只主张“人性向善”。为什么不能不谈呢?因为别人要谈,还要拿这个来挑战仁义。所谓性善论,就是孟子应战的结果。
孟子的性善:人性向善的可能
挑战孟子的这个人叫告子。告子是什么人?不太清楚。但他在《墨子》一书中出现过,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,比孟子大。告子是主张谈人性的,而且主张谈人的天性,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。
据《孟子·告子上》(下引不注者均同),告子说,天生的就叫做“性”(生之谓性)。
孟子反问:天生的就叫“性”,好比白就叫白,是吗(生之谓性也,犹白之谓白与)?
告子说,正是。
孟子又问: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,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吗?
告子又说,正是。
孟子再问:那么,狗性就是牛性,牛性就是人性吗?
孟子说完这话,告子怎么回答?不知道。但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。
第一,不要抽象地谈人性。
抽象地谈,羽毛与雪、雪与玉,没有区别,都是白的。可是,羽之白,与雪之白、玉之白,当真一样吗?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。羽毛与雪、雪与玉的本质区别,就更大。你单单拎出一个相同的“白”来讲,有什么意思呢?难道因为它们都是白的,羽毛的本性就与雪和玉一样了吗?
第二,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。
论天性,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。告子说得很清楚:“食、色,性也。”可见所谓天性,就是吃东西和生孩子。这个动物也会,也想,也能做。如果把这看作人性,岂非“犬之性犹牛之性,牛之性犹人之性”?所以,要么别谈人性,如果一定要谈,就得谈人的社会属性,不能只谈自然属性,更不能把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性。

〇李华摄影
事实上人性问题也不可回避。没有人性做基础,孔子的仁,孟子的义,便都讲不通。这一点,孟子其实心里有数,这才不厌其烦地与告子辩论。
告子说,人性就像杞柳,仁义就像杯棬。以人性为仁义,就像以杞柳为杯棬。杞音起,即杞柳。杞柳是一种杨柳科落叶灌木,也叫白箕柳,枝条可以编筐。棬音圈,意思是盂。
杞柳编筐没有问题,做杯子就讲不通,因此有人认为杯棬可能就是杯圈。这个且不去管他,姑且理解为器物、器皿吧!反正告子的意思,是说让人性服从仁义,就像把杞柳变成器物,乃是一种扭曲。这种观点,与庄子很相似。庄子不是说过吗?违背人性推行仁义,就像把野鸭的腿拉长,把仙鹤的腿截短,是扭曲嘛!
对此,孟子的回答是:扭曲不扭曲,要看怎么做。顺着杞柳的本性做,就不扭曲;反着来,就扭曲。行仁义,也一样。如果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善,就有仁义的基础,就有向善的可能性,那就没有问题,而且应该。问题是:我们有吗?
孟子认为有,告子认为没有。
告子说,人性原本就没有什么善不善的(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)。人性就像水(性犹湍水也),东边开了口子,它就往东流(决诸东方则东流);西边开了口子,它就往西流(决诸西方则西流)。哪有什么善恶之分?
孟子说,不错,水流确实无所谓东西(水信无分于东西),但难道也不分上下(无分于上下乎)?要分的吧!水尚且要分上下,人难道就不分善恶?也要分的吧!怎么分?水性向下,人性向善。这就叫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”。水有往高处流的吗?没有。那么,人也就没有不向善的。这就叫“人无有不善,水无有不下”,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?

当然有问题。人性既然是向善的,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呢?孟子的回答是:环境和条件使然。
孟子说:丰年多懒惰,灾年多强暴,难道是人们天性懒惰、天性强暴吗?不是。是什么?环境和条件“陷溺其心”。这就好比水,原本是往低处流的。如果你把它堵起来,也会上山(激而行之,可使在山)。但是,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(是岂水之性哉)?
水性如此,人性亦然。人性的向善,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,天经地义,毋庸置疑,这就叫“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”。这里的“人性之善”,也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把“之”解释为“的”,则“人性之善”就是“人性的善”。另一种是解释为“去、往”,则“人性之善”就是“人性向善”。
但不管哪种解释,都说明孟子主张“人性向善”。为什么是“人性向善”,不是“人性本善”呢?因为这个“善”,只是可能性。孟子说得很清楚:“乃若其情,则可以为善矣,乃所谓善也。”乃若,就是至于、要说。情,就是人的社会性的本性。
因此,这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:要说人的社会性的本性(人性),那是可以让它善良的。可以为善,这就是善,也就是“性善”。换句话说,性善,就是人性“可以为善”。

〇 李华摄影
现在清楚了。在孟子看来,人性是可以为善的,也是应该向善的。为什么应该?因为善是好的,它就是“人往高处走”的那个“高处”。那又为什么可以呢?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善的可能性。
孟子说,同情心、羞耻心、恭敬心、是非心,这四样东西,是每个人都有的,叫做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”。
恻隐之心就是仁,羞恶之心就是义,恭敬之心就是礼,是非之心就是智。所以,仁义礼智,并不是外部世界或者别的什么人强加给我们的(非由外铄),而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(我固有之),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(弗思耳矣)。其实只要认真想想,每个人都能明白。

同样,只要追求,就能得到,这就叫“求则得之,舍则失之”。舍弃向善可能性的,就成为恶人;反之,则成为好人。这就是人有善有恶的原因。
孟子的这个说法,有什么意义呢?意义就在他为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找到了人性的依据。这个依据在孔子那里是有的,但没有明说,孟子却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。这是孟子对儒学的贡献。不过孟子也有不足之处,就是他没有说清楚,人为什么无须教育,就会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。这些人性当中向善的可能性,怎么就是“我固有之”而“非由外铄”?这一点,孟子说不清楚。
这就留下了一个漏洞,也留下了一个问题。这个漏洞,只能由荀子来填补。这个问题,也只能由荀子来回答。
那么,荀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?

荀子的性恶:化性起伪的智慧
荀子的办法,是把人性分成两半,一半叫“性”,一半叫“伪”。
什么叫“性”?《荀子·正名》说,天生如此的就叫做性(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)。可见所谓“性”,就是人的自然属性。
什么叫“伪”?《性恶》篇(下引不注者皆同)说,但凡“可学而能,可事而成”,事在人为(在人者)的,就叫“伪”。伪,通“为”。可见所谓“伪”,就是人的社会属性。两方面加起来,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“人性”。这个分析,在荀子那里就叫做“性伪之分”。

〇 李华摄影
所谓“性伪之分”,是荀子讨论人性问题的前提。荀子说,孟子主张“性善”,是并不真正懂得人性(是不及知人之性),不知道人性有两个组成部分呀(不察乎人之性、伪之分者也)!这两个部分,一个是自然的、天生的“性”,一个是社会的、人为的“伪”,只有人为的“伪”,才是“善”,天生的那个“性”是“恶”。
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”,是荀子“人性论”的核心观点。这话很容易让人认为荀子主张“人性本恶”。但韦政通先生的《中国思想史》认为,这是“最流行的一种误解”,我也认为是误解。
为什么说是误解?读《王制》篇就知道。在《王制》篇,荀子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分成了四个等级。最低的一等是无机物,其特点是有物质无生命,叫做“水火有气而无生”。略高一等是植物,其特点是有生命无感知,叫做“草木有生而无知”。再高一等是动物,其特点是有感知无道德,叫做“禽兽有知而无义”。最高一等是人,既有物质、生命、感知,又有道德(有气、有生、有知,亦且有义),所以“最为天下贵也”。
人的高贵既然在于道德,荀子怎么会认为“人性恶”?在《非相》篇,荀子甚至明确指出,人之为人,绝不仅仅是双腿直立,身上无毛(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)。他之所以成为人,是因为有道德。这实在是相当科学的论断。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,荀子就已经能够将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”与“社会学意义上的人”区分开来了。
既然如此,荀子怎么会把人的动物性看作人性?所以,我们不能因为荀子说了“人之性恶”这句话,就认为荀子主张“人性本恶”。实际情况是:在荀子那里,性,并不等于我们今天说的“人性”。它充其量只是人性的一部分,而且是人性当中低级的那一部分,即人的自然性或者动物性。高级的部分,荀子叫做“伪”。那才是严格意义上和真正意义上的“人性”。

问题是,荀子这样强调“性伪之分”,究竟有什么意义?
意义就在为礼乐制度寻找人性依据。
在《性恶》篇,荀子说,人之所以要有善(人之欲为善者),就因为他的自然属性是恶(为性恶也),要不得的。怎么就要不得呢?因为如果保留它,人就变成动物了。变成动物又怎么样?无法生存。为什么无法生存?因为人的生存能力远远低于动物。
在《王制》篇,荀子说,人,论力气不如牛(力不若牛),论速度不如马(走不若马),可以说处处不如动物。然而怎么样呢?牛马却为人所用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能够组成社会,牛马不能(人能群,彼不能群也)。
由此可见,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,靠的不是天赋能力,而是社会力量。结论不言而喻:社会如果解体,人就牛马不如。

〇 李华摄影
那么,人为什么能组成社会?
荀子说,因为有秩序。秩序为什么起作用?因为有道德。秩序就是“分”,道德就是“义”,体现道德、保证秩序的就是“礼”,使礼义深入人心的就是“乐”。它们也都是“伪”。伪,不是“虚伪”,而是“人为”,也就是“改造”。没有这个改造,人就不能从动物变成人,不能把动物性变成人性,这就叫“无伪则性不能自美”(《荀子·礼论》)。性不能自美,又怎么样?人就变成动物,甚至连动物都不如,没法生存了。所以,礼乐制度,能不重要吗?
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荀子比孔子和孟子高明、深刻的地方。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